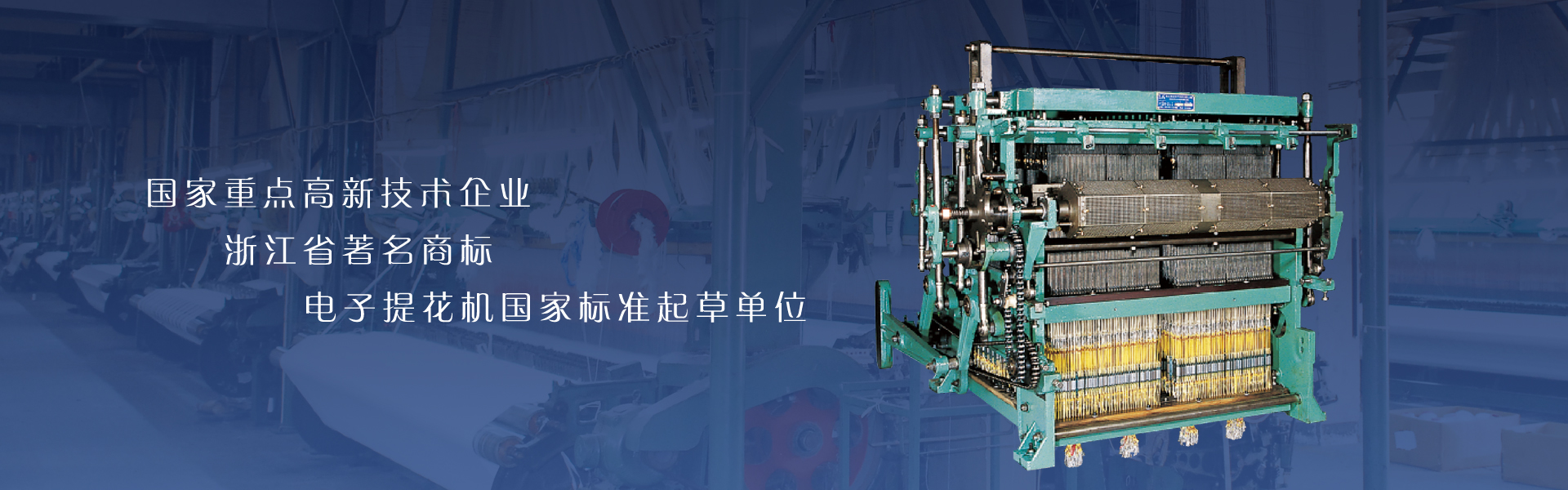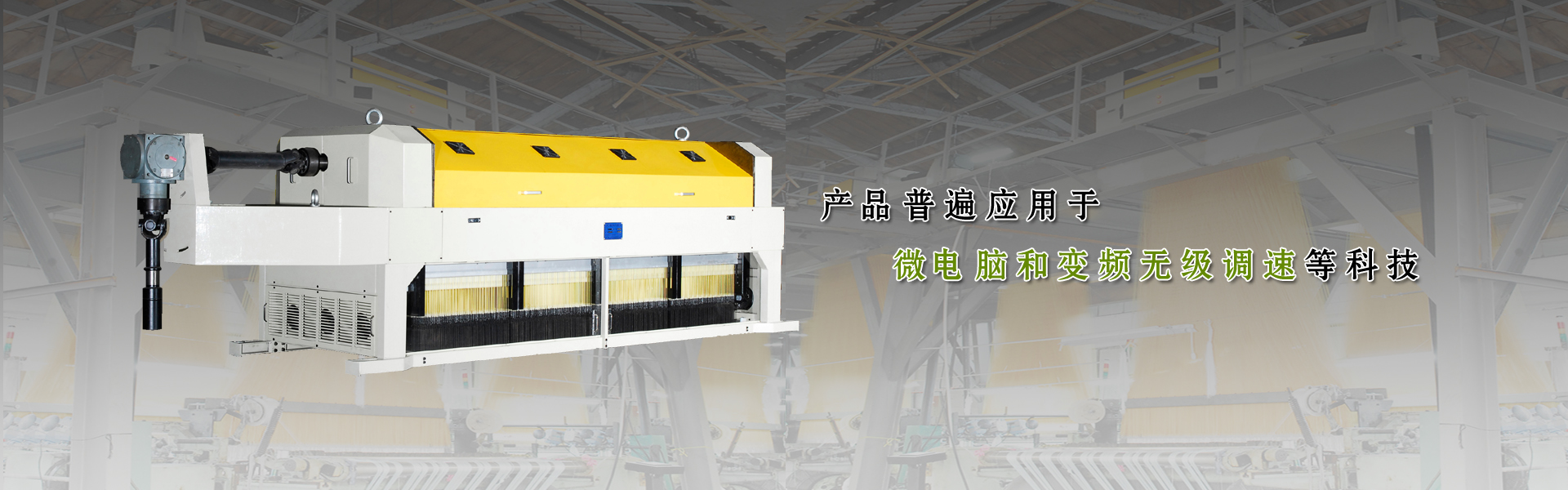ayx爱游戏官方下载:纺织厂恶魔厂长欺凌!女工死磕讨血泪债
ayx爱游戏全站app:
1988 年大暑,城镇纺织厂的铁皮顶棚被日头烤得发烫,三十台缝纫机 “哒哒哒” 的轰鸣裹着棉絮飘在车间里,吸进肺里都觉得扎得慌。陈春杏直起发酸的腰,右手在背面揉着腰椎 —— 从早上七点到现在,她现已踩坏了两卷底线,指尖被钢针扎破的当地,血珠渗进的确良布料,晕开个暗红色的小点,像落在蓝布上的苍蝇屎。
“新来的!发什么呆!” 一声吼炸在头顶,陈春杏吓得手一抖,钢针直接戳进食指。她匆忙把手指含进嘴里,铁锈味混着唾液在舌尖散开,昂首就看见张满仓的瘸腿卡在她凳子缝里。这厂长穿件灰西装,领口别着枚镀金首领像章,油光水滑的头发用发蜡抹得溜顺,连电风扇吹过都没动一下,只要左脸的金牙在日光灯下闪着晃眼的光。
“这线走歪半毫米,你知道要赔多少钱?” 张满仓折腰时,烟酒混着汗臭的滋味喷在陈春杏后颈,粗糙的拇指蹭过她耳垂上的朱砂痣,那力道像要把痣抠下来,“抵得上你家三亩甘蔗地的收成,够你弟念半年书。” 他的瘸腿往陈春杏大腿外侧顶了顶,西装裤冲突布料的 “沙沙” 声,听得她浑身发僵。
陈春杏想起三天前进厂的容貌。招工处的水泥墙上,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 的红漆褪得只剩淡粉色,管人事的李桂芬捏着她的初中毕业证,嘴角撇得能挂油瓶:“虚岁十八?这细臂膀细腿,能搬动三十斤的布卷?” 宿舍管理员赵淑兰脸上的烫伤痕像条蜈蚣,说话时疤都在动,最终是张满仓拍了桌子:“留下吧,也算照料勇士家族 —— 她爹修水库被塌方压死的。”
缝纫机忽然被关掉,踏板的惯性让陈春杏的膝盖撞在金属杆上,疼得她倒抽凉气。张满仓的瘸腿还抵在她腿边,手摸着她按在布料上的手背:“这批货要出口东南亚,今晚加个班。” 他的喉结上下滚了滚,长着黑毛的手背蹭过她胸前第二颗纽扣,“干得好,下个月给你转正式工,今后便是吃商品粮的人了。”
车间西北角的吊扇忽然停了,陈春杏听见自己咽口水的动静。三排外的赵淑兰冲她使了个眼色 —— 昨日午休时,这女性还悄悄教她把月经带藏在工服夹层里,“厂里上厕所要挂号,超越五分钟就扣五毛钱,这月我都被扣了三块了。” 可现在,赵淑兰却低下头猛踩踏板,钢针在蓝布上扎出歪扭的线脚,像条断了的蛇。
暮色把窗玻璃染成橘红色时,张满仓又晃到陈春杏工位前。她正用牙齿咬断线头,猝不及防被他捏住手腕。“手这么凉,是不是贫血?” 张满仓的金表带硌得她手腕生疼,“库房里有红糖,跟我去拿点补补。” 他的瘸腿在过道里拖出 “吱呀” 的冲突声,本来 “哒哒” 响的缝纫机忽然全停了,车间里静得能听见窗外麻雀的叫声。
穿过堆着碎布头的走廊时,陈春杏数着墙上的裂缝。第七道裂缝正对着女厕所,磨砂玻璃后,李桂芬的烟头忽明忽暗,烟味飘过来,混着厕所的骚臭味,熏得她鼻子发痒。库房铁门推开的瞬间,霉味裹着樟脑丸的滋味扑面而来,成捆的确良布料堆在墙角,在暮色里泛着青白的光,像极了母亲咳在珐琅盆里的痰。
“把门关上。” 张满仓的动静忽然变调,没了方才的放肆,多了点鄙陋的沙哑。陈春杏回身时,正好撞上他鼓胀的啤酒肚,后腰抵在冰凉的缝纫机台面上,寒意顺着的确良衬衫往骨头缝里钻。张满仓的金牙咬住她右耳垂,带着烟味的唾液沾湿了朱砂痣:“别叫,你娘还等着你来寄哮喘药,要是丢了作业,她的药钱从哪来?”
成匹的布料忽然 “哗啦” 坍毁,陈春杏昂首,看见天花板上的灯泡晃得凶猛。张满仓的假领子擦过她锁骨,金属拉链勾住她衬衫下摆,“刺啦” 扯破个小口。她想起离家那天,村长媳妇往她包袱里塞了两包卫生纸,手都在抖:“在城里被人欺压就忍忍,你弟还要靠你供着上学,别跟人闹僵。”
女工宿舍的霉斑在旱季长得飞快,墙角的霉点像张鬼脸,盯着陈春杏的铁架床。她刚躺下,就听见李桂芬的铜钥匙串在走廊里 “叮当” 响,八张铁架床跟着轰动。张满仓的瘸腿脚步声混着雨点击打石棉瓦的动静,像钝刀在肉上划,听得人心里发毛。
“突击检查!查违规私藏物品!” 李桂芬的解放鞋踩在陈春杏床尾,脸上的疤痕在闪电里泛着紫色。她一把掀开陈春杏的枕头,两根用卫生纸包着的月经带掉在地上,李桂芬尖着嗓子喊:“203 床陈春杏!违规私藏棉制品!按厂规扣三天工钱!” 其他女工都缩在蚊帐里装睡,连呼吸都放轻了。
“李姐,不是我要藏,” 陈春杏攥着发潮的床布,动静发颤,“劳保科三个月没发卫生棉了,我不必这个,总不能……”
“还敢顶嘴?” 张满仓的茶渍牙咬碎烟头,金表链扫过陈春杏的锁骨,冰凉的金属硌得她生疼,“厂规第十条,顶嘴领导加倍扣钱,你这月工钱本来就没多少,再扣,怕是连回家的车票都买不起。”他的塑料雨衣贴在陈春杏臂膀上,雨水渗进衬衫,冻得她臂膀发麻。李桂芬忽然扯开她的领口,显露前天被张满仓掐出的淤青:“这伤哪来的?是不是跟男工钻草垛鬼混了?”
三十瓦的灯泡在风雨里晃个不断,陈春杏看见赵淑兰躲在被窝里颤栗。便是这一个女性,昨日还在锅炉房跟她哭:“我男人上一年在厂里修机器,被齿轮轧断了手,张瘸子说抚恤金在他手里,要我听他的话才给,否则就说我男人是违规操作,一分钱都拿不到……” 可现在,赵淑兰用棉被堵住耳朵,连看都不敢看她。
“问你话呢!哑巴了?” 李桂芬的指甲掐进陈春杏的肩胛骨,疼得她眼泪都快掉下来。张满仓的瘸腿忽然挤进她两膝之间,雨衣上的樟脑味呛得她咳嗽。走廊里传来布鞋跑过水洼的动静,接着是 “咚” 的一声闷响 —— 有人从二楼跳窗跑了,大概是怕被牵连。
张满仓掏出块牡丹牌手帕,擦了擦陈春杏脑门的汗,手帕上的头油味直往她鼻子里钻:“年轻人不懂事,犯了错改了就行。” 他忽然把帕子塞进陈春杏嘴里,“咬住,省得等会儿查东西的时分,你乱说话坏了厂里的规则。” 李桂芬蹲在地上翻陈春杏的珐琅盆,里边只要半块硫磺皂和三张快过期的澡票。
“啪嗒” 一声,铁皮饼干盒被撬开,里边的全家福相片掉在积水里。张满仓的瘸腿正好碾在相片上弟弟的笑脸上,鞋底的泥把弟弟的脸糊成了黑团:“你爹是勇士,你更要留意风格,别给勇士丢人。” 他的塑料雨衣擦过陈春杏的大腿内侧,动静压得很低:“下月转正的名额,我给你留了一个,就看你懂不懂事……” 窗外的惊雷 “霹雷” 一声,把后半句话炸得没了影。
陈春杏数着李桂芬没收的东西,心里像被针扎。当张满仓的手伸向铁架床第三根横梁时,她忽然挣扎起来 —— 那里藏着母亲亲手缝的碎花内裤,布料是她出嫁时的陪嫁,母亲说 “带着这个,就像娘在你身边”。
“按住她!别让她乱动!” 李桂芬的解放鞋踩住陈春杏的脚踝,力道大得像要把骨头踩碎。张满仓的瘸腿膝盖顶住她的胃,金表带刮破她的手腕,血珠渗进表带的缝隙里。铁架床在拉扯中移了位,显露墙缝里塞着的黄草纸,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七个正字 —— 每个笔画,代表她被张满仓扣掉的一天工钱。
碎花内裤被张满仓甩到窗边时,布料 “刺啦” 裂了个口。他抓起内裤凑到鼻子前闻了闻,金牙在闪电里闪着光:“茉莉香?比赵淑兰的雪花膏味正多了。” 陈春杏看见赵淑兰的膀子在被窝里抖得更凶猛了,大概是想起了自己被欺压的姿态。
瓢泼大雨把石棉瓦砸得 “噼啪” 响,陈春杏数着李桂芬钥匙串响的次数。第八声 “咔嗒” 响起时,张满仓忽然抽走她嘴里的手帕:“厂里要培育你当质检员,今后不必再踩缝纫机了。” 他的瘸腿蹭着陈春杏的小腿肚,动静里满是估计,“明日夜班来库房,我考你认料子,考过了就给你转正。”
宿舍铁门 “哐当” 关上时,陈春杏摸到床缝里的半截铅笔。赵淑兰哆哆嗦嗦递来张皱巴巴的草纸,上面是她用铅笔摹写的《劳动法》条文,字歪歪扭扭的,“同工同酬” 四个字被雨水泡得发淡。陈春杏攥着草纸,眼泪掉在 “制止克扣薪酬” 那行字上,把纸都打湿了。
清晨三点,陈春杏在厕所隔间里冲刷身体。李桂芬的铜钥匙串在门外闲逛,“就给你三分钟,超时扣钱!” 她用鞋跟敲着水泥地,动静尖得像针。陈春杏盯着手腕上的表带印,猛地发现张满仓的金表链缺了两节 —— 那截刻着 “上海” 二字的链节,此时正卡在她床板的裂缝里,是方才拉扯时刮下来的。
暴雨把库房的铁皮房顶砸得像在敲鼓。陈春杏数着配电箱跳闸的次数,第三次漆黑降暂时,张满仓的瘸腿现已卡在她两膝之间。成卷的确良布料在闪电里泛着青白的光,她想起招工体检那天,李桂芬用冰凉的听诊器压在她胸口:“肺活量缺乏啊,要是再差口气,就无法进车间了。”
“今日考你认料子,” 张满仓的塑料雨衣擦着陈春杏的后背,金牙咬开她衬衫第三颗纽扣,湿润的布料贴在皮肤上,又凉又黏,“这是出口的精梳棉,一平米能卖五块钱,比你爹当年一天的工钱还多。” 他的手摸着陈春杏的腰,力道越来越大。
停电前半小时,赵淑兰悄悄塞给陈春杏半块桃酥,油纸里裹着库房的钥匙,动静压得很低:“张厂长说,你考过了就给转正,还能把扣你的工钱补回来。” 这女性的眼泡肿得像核桃,工装裤膝盖处沾着墙灰,大概是又被张满仓骂了。
雷声碾过房顶时,张满仓的瘸腿忽然发力,陈春杏的太阳穴撞在缝纫机头,血珠渗进鬓角的碎发里。张满仓嗓子里滚出污浊的笑,金表链缠住她的手腕:“这表是上海牌机械表,当年托人买的,花了我三个月薪酬,比你爹的命都值钱。” 他的金牙咬开陈春杏的胸罩搭扣,的确良衬衫在挣扎中裂成了两半。
陈春杏的指甲抠进缝纫机油槽里,摸到半切断针。张满仓的瘸腿压住她的脚踝,塑料雨衣蒙住她的脸,闷得她喘不过气:“敢叫一声,我就托人把你弟送到少管所,说他偷厂里的铜纽扣 —— 你知道的,少管所里的日子可不好过。” 他的要挟混着雨腥味灌进陈春杏的鼻子,“李桂芬都看见了,你偷拿厂里的劳保棉,按厂规能把你送派出所。”
闪电劈开库房天窗的瞬间,陈春杏看见张满仓手腕上缺了的表链。那截刻着 “1988” 的链节,还卡在他手腕结痂的抓痕里 —— 大概是之前欺压其他女工,被人抓的。成匹的布料忽然又塌了下来,压在张满仓背上,他的假牙滑到陈春杏锁骨处,口水在沾着茉莉香皂味的皮肤上,留下道黏糊糊的印子。
“赵淑兰!你死哪去了!” 张满仓忽然冲着漆黑吼。库房铁门 “吱呀” 响了声,赵淑兰举着马灯的身影在暴雨里晃悠,马尾辫散了半边,的确良工装被雨水泡得贴在身上,显露腰间紫红的掐痕,看得陈春杏心里一揪。
陈春杏的哭喊被雷声盖得结结实实。张满仓的瘸腿压住她的手腕,金表链在缝纫机台面上刮出 “刺啦” 的动静:“看着!你给我好好看着!” 他冲赵淑兰喊,“学学人家怎样当质检员,别总笨手笨脚的,连块布料都认不清!” 赵淑兰手里的马灯忽然歪斜,火油滴在陈春杏挣扎的小腿上,烫得她直抽气。
的确良布料缠住陈春杏脚踝时,她想起离家那天的场景。村长媳妇往她包袱里塞卫生纸的手在抖:“你娘咳血的事,别跟厂里说,说了他们必定不必你。” 此时张满仓的指甲正掐进她大腿内侧,疼得她浑身颤栗:“你爹是勇士,你就该报效厂子,这点小事都不乐意,对得起你爹的名声?”